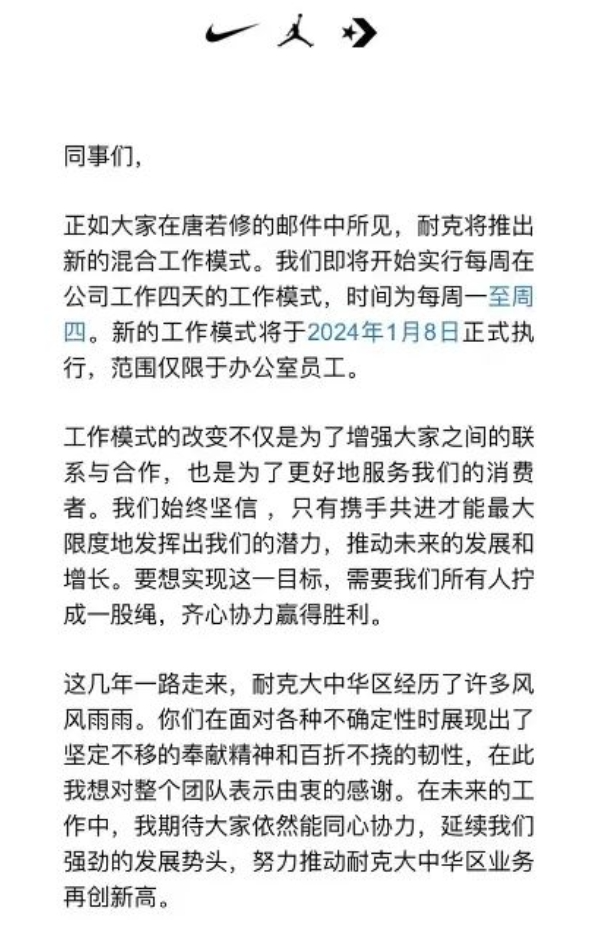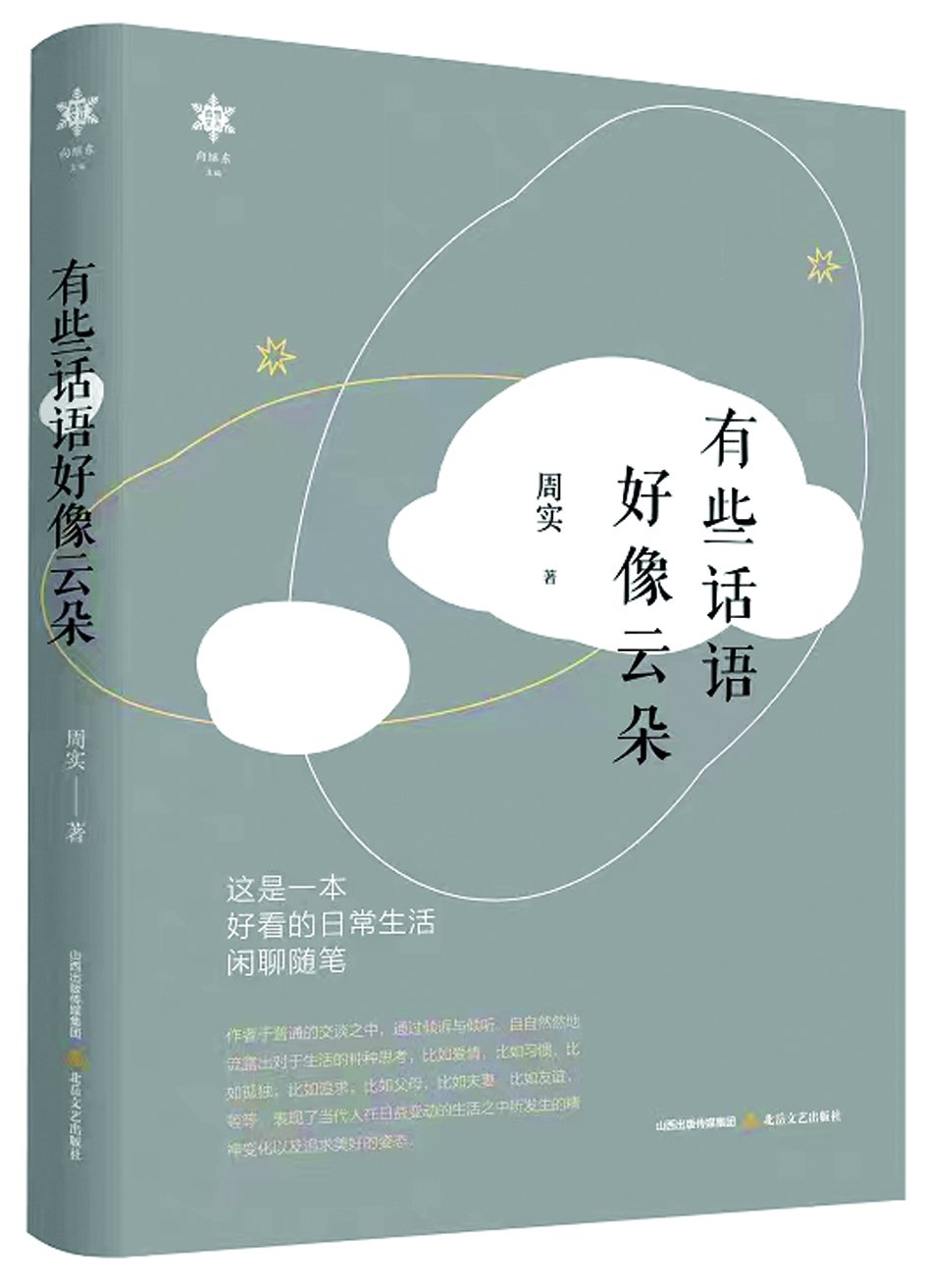“的是”那些闪亮的珍珠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安徽商报的那些闪亮的珍珠,如果您对那些闪亮的珍珠感兴趣,请往下看。
■私读
《黄金牡丹》
◎须兰/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钱红丽
家里至今存有三毛的书。几十年过去,《撒哈拉的故事》历历在目:满身泡沫地洗着澡,突然没水了,拿条毛巾随便擦擦,也是知足的日子;《万水千山走遍》里,在欧洲的一个缓坡处,遇见一座破败小教堂,她走进去,跪在台阶上,泪水止不住的翻涌,都是心碎的日子……这些细绒毛一样的琐屑,泥土一样匍匐在记忆沟回,几十年不褪色。谁的青春期不曾迷过三毛?——纵然如今自个也能书写了,也不要粉饰当年初初涉世的路。
那样蓬勃的一字打头的年纪,不仅看三毛,还涉猎岑凯伦、玄小佛——她们,对于空无稚嫩的我们,都是源头性滋养。
实则,我读书是从诗歌起步的,从舒婷、王小妮、陆忆敏,到古希腊的萨福,再到北欧女诗人埃迪特·索徳格朗。
总是被那些简短、迷离的句子,无端地激荡着,那些分行的诗句犹如一畦畦沃土,一颗颗滋养着书写的种子。
读诗的岁月,也快,日子到了九十年代,目光自然地投向中国当代的女作家们:迟子建、林白、陈染、叶广苓、简媜、朱天文,以及同龄人魏微等。
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真是清正纯净,她的《亲亲土豆》《雾月牛栏》《一匹马两个人》等,一生忘不掉,始终氤氲着一份情怀,关注底层的小我,慈悲和怜悯在岁月里发酵,时时被她干净的文风所激荡——文学是可以洗礼一个读者的灵魂的。
其次是陈染,她小说里的黛二小姐颇相像于作者本人,孤独,寡言,慢热,偏重于内倾主义的精神生活,家里寂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见。这些年,迟子建、林白依然孜孜创作,独不见陈染消息,挺想念她孤冷的文风。叶广苓是满族,本姓“叶赫那拉”,擅长家族题材的小说。有几年,她的小说题目皆取自纳兰容若的词——《谁翻乐府凄凉曲》《梦也何曾到谢桥》……家族中那些格格们的命运跌宕沉浮,读来心醉神迷。自从叶广苓挂职当副县长以后,她小说的特质颇接近于报告文学的现实主义,与先前的家族题材不可同日语。这一回,算翻过去了。
与之同时关注的,还有简媜、朱天文。前者的《渔父》《四月烈帛》,字字情深浓烈,宛如欧姬芙的花卉册页,饱胀而瑰丽,鲜艳欲滴,恰好与青春期的荷尔蒙一拍即合,不比人至中年,于文风上,口味急转直下于寡寒素淡。
说着说着,近三十年往矣。
那年,简媜出镜于深圳某书城,清瘦,苍茫,白雪满头,我看着,无端感念。还有朱天文,一双手伸出来,遒劲沧桑,睡眼惺忪的疲态。
到底,我这个做读者的也老了,何况她们?电脑收藏夹里有朱天文年轻时在洛杉机的一张留影,两根细麻花辫荡在胸前,一脸的纯净天真,青春迫人。
一切俱往矣。
当年,“70后”的概念风嚣尘上时,唯独喜爱其中的魏微,如今,她也少写了。曾经的长篇《一个人的微湖闸》(单行本更名为《流年》),线性结构,充满生命的成长,读来风烟俱净,如诉如告,掩卷不能,一如秋雨凭栏寸心相知。
最不应忘记的是——须兰。
须兰生于六十年代末期,上海人,独一无二的小说家。她的小说有氛围,弥漫着古意和宿命,《石头记》《宋朝故事》《红檀板》《纪念乐师良宵》《奔马》《白牛》《少年英雄史》《曼短寺》……以及后期的《千里走单骑》,文气宽厚,隐匿女性的阴柔,跟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类似,行笔似男人,粗犷宽阔。
须兰早已搁笔,自求学香港后,再没回来。其间出过一本随笔《黄金牡丹》。在香港当了编剧。据说《投名状》的首席编剧,就是“隐身”的她。
人生意味都在不远的天边吧。一个擅长历史题材的小说家是该隐于世俗的大众视野之外,不艳,不燥,一如她曾经评价过的汉、魏晋六朝、唐、宋等朝代:“才气纵横又有点儿醉生梦死,繁华中透着冷清”。
一个立志书写的人,就应该过得冷清。
须兰的小说目前不大好找了,旧书网可能尚有零星。分别是《须兰小说选》《思凡》等。
写到这里,不免感念——纵然热爱文学如许经年,竟未曾厌倦过。活得如此芜杂平凡,人的一生难免平淡潦草,庆幸的是,我们总是心有所寄。《古诗十九首》里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活于世,忧怀难免,但,有了文字的相伴,即便愁忧烦闷,也是有分量的日子。
文字是可以塑造一个人性情的,从这些有着珍珠般闪亮的女作家们的文字里,我一点点学会了审美,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自处——孤独地与自己相处,时时反省自己,但,不诋毁自己,纵然在繁华的冷清里,也是体面与尊严的,感谢她们。
好了,关于那些闪亮的珍珠就讲到这。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科技金融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相关文章
- “尔森”用心倾听大自然的神秘邀约
- “考生”硕士统考发布报名提醒 考生需及时自查,抓紧时间修改
- “合肥市”“柿柿如意,柿如破竹”…… 高三学子“花式解压”
- “肌肉”磁铁刺激疗法可“对齐”肌肉纤维
- “低价”第15个双11:电商巨头争夺“最低价”、取消预售、开放生态
- “犯罪嫌疑人”湖南新化砍伤一对夫妇的犯罪嫌疑人落网,4人涉嫌窝藏罪被批捕
- “中国移动”中移动市场详情:合作伙伴大会重要发言及发布、反诈、5G应用获奖
- “血液”简单的血液检查调整可使重症监护治疗更安全
- “南充市”落马公安局长收受财物1365万被判7年:悔称利欲熏心,“金钱大厦”瞬间倾覆一生毁灭
- “高粱”河南固始有执法人员带人偷高粱?当地回应:涉事人员为行政执法大队人员,正调查
- “都是”A股的觉醒之年!
- “万元”中大型纯电SUV再添一员:昊铂HT开启预售
- “小时”抖音“小时达”上线独立入口 将动谁的奶酪?
- “屏幕”消息称iPhone 17系列屏幕有重大升级:“胶囊屏”时代终结
- “物理”青少年该如何学习物理?“物理网红”张朝阳称要从小激发好奇心
- “订单”9 月网约车行业共收到 7.93 亿单,享道出行订单合规率最高
- “惠普”惠普亮相Tech G 2023,觉醒行业新生态
- “二手”CCS Insight:预计2023年底市面上将有13亿部iPhone在流通 超过一半都是二手机
- “学报”患病后,他高薪聘请研究人员,“没有一个人工作超过3个月”
- “俄罗斯”运营商财经网康钊:被美国最新列入实体清单的都是什么中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