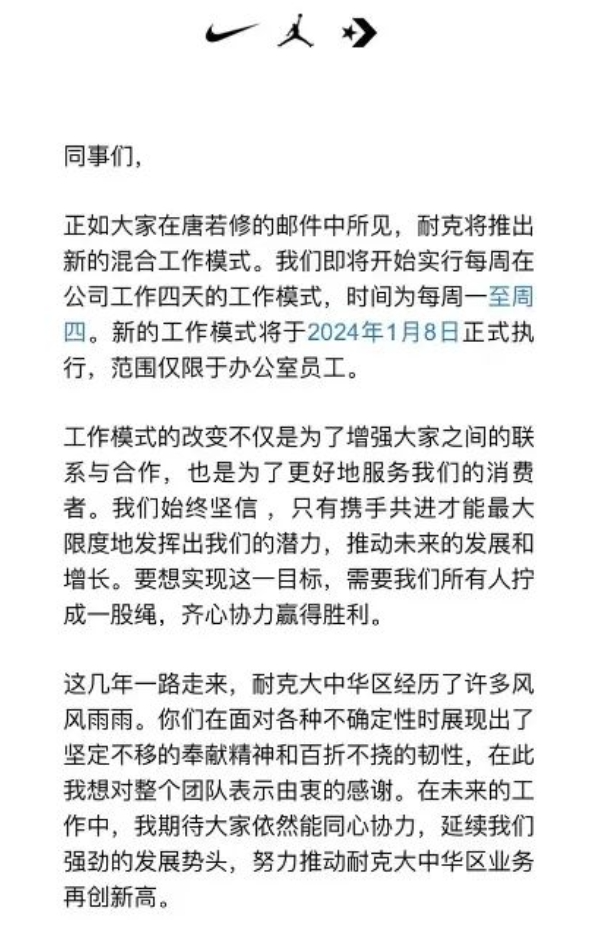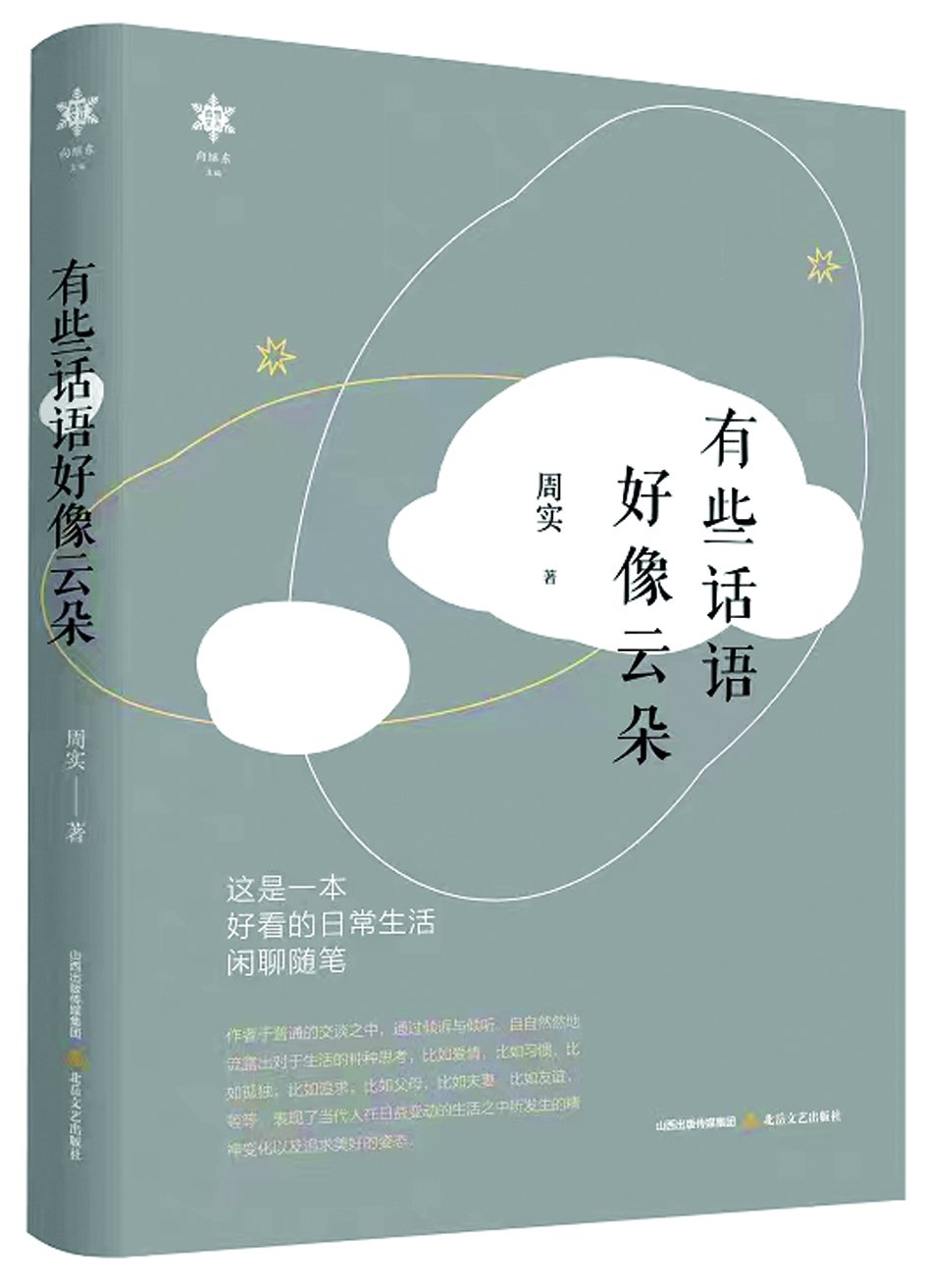“南越”全洪:南越国铜镜是汉越文化融合的实证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新快报的全洪:南越国铜镜是汉越文化融合的实证,如果您对全洪:南越国铜镜是汉越文化融合的实证感兴趣,请往下看。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今年是广州考古70周年,也是南越文王墓发掘40周年;而在2022年10月,“广东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王墓”也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秦汉时期统一的大背景下,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历史文化面貌,正在深化呈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岭南地区考古学研究的重大学术课题”,日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全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全洪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项目“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子项目的岭南部分主要负责人,从事岭南考古30多年,对此重大课题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研究。
如何逐步复原南越时期文化融合面貌?铜镜,在考古研究中,是一个很好的载体。记者曾读过全洪此前发表的《南越国铜镜论述》,该文至今仍是南越国时期铜镜研究的代表之作。本次,结合当年资料,全洪进一步给记者做了专业解读。
1
照镜,秦军带来的风俗
越人本没有镜。秦人来了,他们带着铜镜来了,后来,南越人便也学会“照镜”了。
铜镜,岭南文化变迁的载体。
在《南越国铜镜论述》(以下简称《论述》)中曾有言:“铜镜作为反映岭南文化变迁的载体,从某个侧面,体现了汉文化对越人生活习俗方面的影响。”全洪介绍,在典型的越人墓里都不见或少见铜镜,表明越人没有使用铜镜的习惯。他特别向记者强调:“岭南出现铜镜,时间上限要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说起。”
岭南出现铜镜,由秦始皇“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开始,是秦军带来的风俗。《论述》中认为,“秦统一岭南和赵佗建立南越国以后,越文化逐渐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同化。也就是说,南越出现铜镜不是一般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接触所产生的现象,而是由于文化同化所造成的。”
全洪进一步向记者说明:“同化是文化人类学的术语,现在更多是用‘文化融合’来表述这种从生活习俗到思想意识的变化。”
记者也留意到《论述》中所提及的“文化影响的波次现象”,就是,当时,以都城番禺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一种新型的汉越融合的南越文化,新的文化由此传播出去,越靠近中心地带,受此文化的影响就愈大,越远则越小,所以,“广州发现的铜镜最多,贵县、贺县、肇庆等地也有,岭南的东部、东北部、西部以及西南部和越南北部就未发现铜镜,也没有典型的汉越融合的文化特征。”
2
“与时俱进”的铜镜
是“断代”的好工具
那么,这个时期的岭南铜镜,又是如何分类的呢?
《论述》从器物类型学角度,大致将其分为战国中晚期、战国末期-秦代、秦汉之际-文景时期以及武帝时期四个历史时期。在南越国时期则可分作秦汉之际、文景时期和武帝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镜式主要是战国和秦代的铜镜,是秦兵、汉军和南迁的中原人带来的,镜型有素地镜、山字纹镜、龙凤纹镜和带托镜等;第二阶段的镜子有龙纹镜、蟠螭纹镜和彩绘镜等;第三阶段的镜式以草叶纹镜为主,这种镜可能在景帝后期或武帝初期就产生,到武帝中期铸行五铢后定型,成为汉式镜的典型代表。”
当时,发现于广州、贵县、贺县和肇庆等地的南越国时期铜镜,有120余枚,“我依据镜背的纹样把它们分为14种类型,时至今日,随着出土数量的增加,这14种分型,是依然适用的,”全洪对记者说。
他说:“铜镜阶段性的划分,再结合其他文化因素和考古材料,对分析判断南越墓葬的年代有很大帮助。这也是我们选择铜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的时段性非常明显。从考古器物类型学角度来说,铜镜与其他带铭文的铜器一样,对断代分期或者分阶段有重大指标性意义。”
众所周知,陶器是分期断代的主要器物,“但陶器使用时间延续较长,也就是说,有些器型、纹饰的变化会较显‘迟钝’——可能已经进入不同时期了,但上一个阶段的陶器仍被使用。铜镜的样式变化则较为迅速,这与上层意志以及审美观念有关。例如,楚镜有其自身风格;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当然就推行秦镜;到汉朝建立,自然也会相应改变、出现‘天地人’等纹饰元素。”
全洪举了一个铜镜“与时俱进”的例子——
汉代“规矩纹”镜,又被称为“博局纹”镜,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天象对自然的理解;到了西汉中晚期,求仙、求长生不老的思想由高层贵族慢慢向大众普及,所以西汉晚期或东汉时,描绘神仙的纹饰就在铜镜上出现。铜镜上的纹饰反映了时人的思想意识。
3
铜镜,“王的收藏品”
铜镜不仅可以“断代”,还透露着其主人的身份和种族等重要信息。
记者留意到《论述》中有一句话:“出土铜镜数量最多的墓型是单室竖穴木椁墓。”这是为什么呢?全洪解释:“单室竖穴木椁墓,也是南越国数量最多的墓葬。这些墓主,大多数是南越国各级官吏或其他统治阶级,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在已发现的‘墓主’中占比最多,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和财力。”
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看待铜镜的?“应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必备用具。东汉·班固《汉书·张敞传》里就有个典故‘张敞画眉’,张敞替妻子画眉毛,现在常用于比喻夫妻感情好,这就说明汉代闺阁之中,铜镜已成为部分人的日常生活必备用具。”
所以,许多墓葬中,都出现了铜镜的身影。“截至1995年,已公布的南越国时期墓葬中有78座墓共出土了121枚铜镜。除了南越王墓一墓出39枚较为特殊外,其余多为一墓一镜,个别出2枚。(据《论述》)”
“陪葬使用铜镜,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喜爱的、流行的、贵重的物品的态度。不同区域的习俗,也能体现出来。”他进一步解释。
铜镜也是“王的收藏品”。记者在《论述》中看到,如上所述,南越文王墓不仅一墓就出39枚铜镜,还出土一枚特别的“带托镜”,“因墓主生前好收集古玩,墓中大量前朝的珍贵物品,这面镜子当是赵眜收藏的战国铜镜”。
4
南越国也有自己生产的铜镜
最后,我们谈到南越国时期这些铜镜的来源。
全洪认为,南越国时期的铜镜数量较多,品种较齐,但绝大多数铜镜是由内地输入,而非本地铸造。“因此,不能直接推论其演变的过程。然而经过与全国各地的铜镜进行比较,这批铜镜对我国铜镜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铜镜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南越时期的铜镜不仅展示了区域性的铜镜发展史,同时也反映出与全国铜镜史的发展轨迹是步调一致的。”
“南越国时期的铜镜基本上是以汉代出现的新型镜式为主的,如龙纹镜等。虽然有一批战国时期的秦式和楚式铜镜遗留下来,而战国镜沿用到秦汉时期也是全国性的。到了汉武帝改制以后,中原地区,特别是长安、洛阳等地出现新的蟠螭铭文镜和草叶纹镜等新的镜式时,南越国的后段也同步出现。总而言之,南越国人所使用的铜镜是紧随着同期中原内地的人们所使用和流行的镜式的。”
随后,他着重强调,还有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不容忽视,就是,南越国也有自己生产的铜镜。
“我这篇文章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指出有几枚铸造不精、纹饰粗糙的铜镜,可能是南越本地仿制的。”记者看到,《论述》中是这样写的:这几枚铜镜与其他镜子相比较,除了纹饰不够精致外,布局方面也有不同。南越王墓E121、E98、F31中的几面镜子,都存在线条滞钝,纹饰不够清晰、明快,铸造较粗的现象。而还有三枚铜镜,就是研究文章中分类的Ⅺ型镜,其纹饰相同,大小相近,铸造粗陋,主体纹饰不易辨认。从它有方框及方座四角外伸四叶看,显然是受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偏后流行的蟠螭纹铭文镜和草叶纹镜的影响而铸造。由于只见于南越国,未见于其他地方,可能是南越国的工匠模仿新出现的镜式铸造的。
“更重要的是,”他补充说道,“其实除了类型学判断之外,我们还做了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其成分与楚镜不同,应是本地制作,但工艺水平与中原内地仍有差距。这也表明随着越文化融入汉文化之中,南越当时逐渐掌握了部分铸铜技术。”
在这一场岭南铜镜从无到有、从外来到“自制”的精彩历程中,全洪认为,岭南地区使用铜镜乃中原汉人南徙即“文化融合”的结果,南越国时期的铜镜,为研究秦平南越之后岭南进入崭新发展阶段所引起的南越文化变迁、汉越文化融合,提供了实物佐证。
好了,关于全洪:南越国铜镜是汉越文化融合的实证就讲到这。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科技金融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相关文章
- “尔森”用心倾听大自然的神秘邀约
- “考生”硕士统考发布报名提醒 考生需及时自查,抓紧时间修改
- “合肥市”“柿柿如意,柿如破竹”…… 高三学子“花式解压”
- “肌肉”磁铁刺激疗法可“对齐”肌肉纤维
- “低价”第15个双11:电商巨头争夺“最低价”、取消预售、开放生态
- “犯罪嫌疑人”湖南新化砍伤一对夫妇的犯罪嫌疑人落网,4人涉嫌窝藏罪被批捕
- “中国移动”中移动市场详情:合作伙伴大会重要发言及发布、反诈、5G应用获奖
- “血液”简单的血液检查调整可使重症监护治疗更安全
- “南充市”落马公安局长收受财物1365万被判7年:悔称利欲熏心,“金钱大厦”瞬间倾覆一生毁灭
- “高粱”河南固始有执法人员带人偷高粱?当地回应:涉事人员为行政执法大队人员,正调查
- “墓葬”南越国贵族墓葬是怎样营造的? 聚焦黄埔镬盖顶岭最新考古发现
- “岭南”没骨法新探作品展
- “附子”岭南炮天雄炮制技艺:巧手炮制 毒药变食材
- “文物”志愿讲解者陈浩:我是这样 让文物“活”起来的
- “岭南”岭南派要有所发展 应让写实更到位
- “铜镜”粤博讲座:广东铜镜价值仍被大多数人忽略
- “中医药”岭南中医药博物馆发布藏品征集公告
- “南越”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
- “广州”从这些文物读懂“广州智慧”
- “工作”“五一”我在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