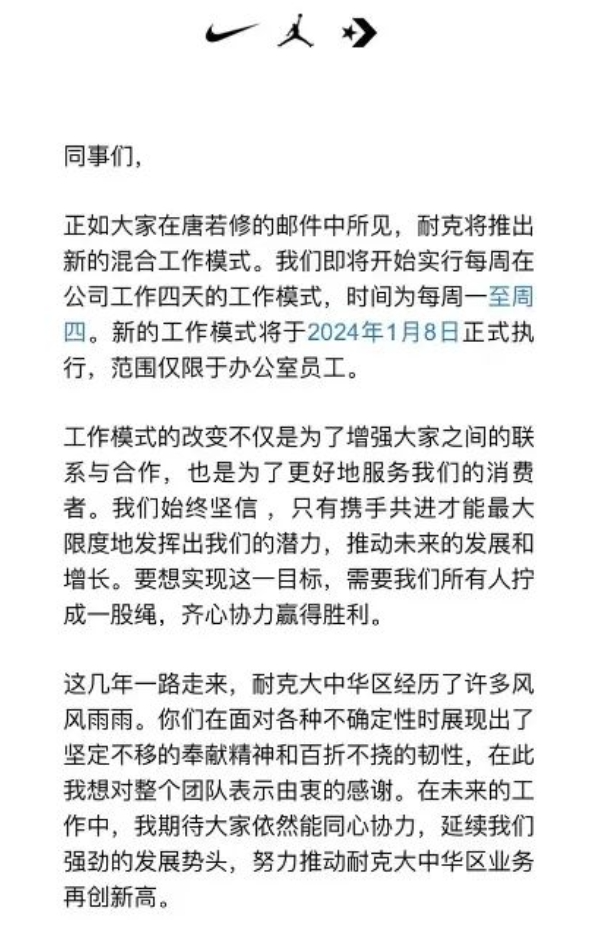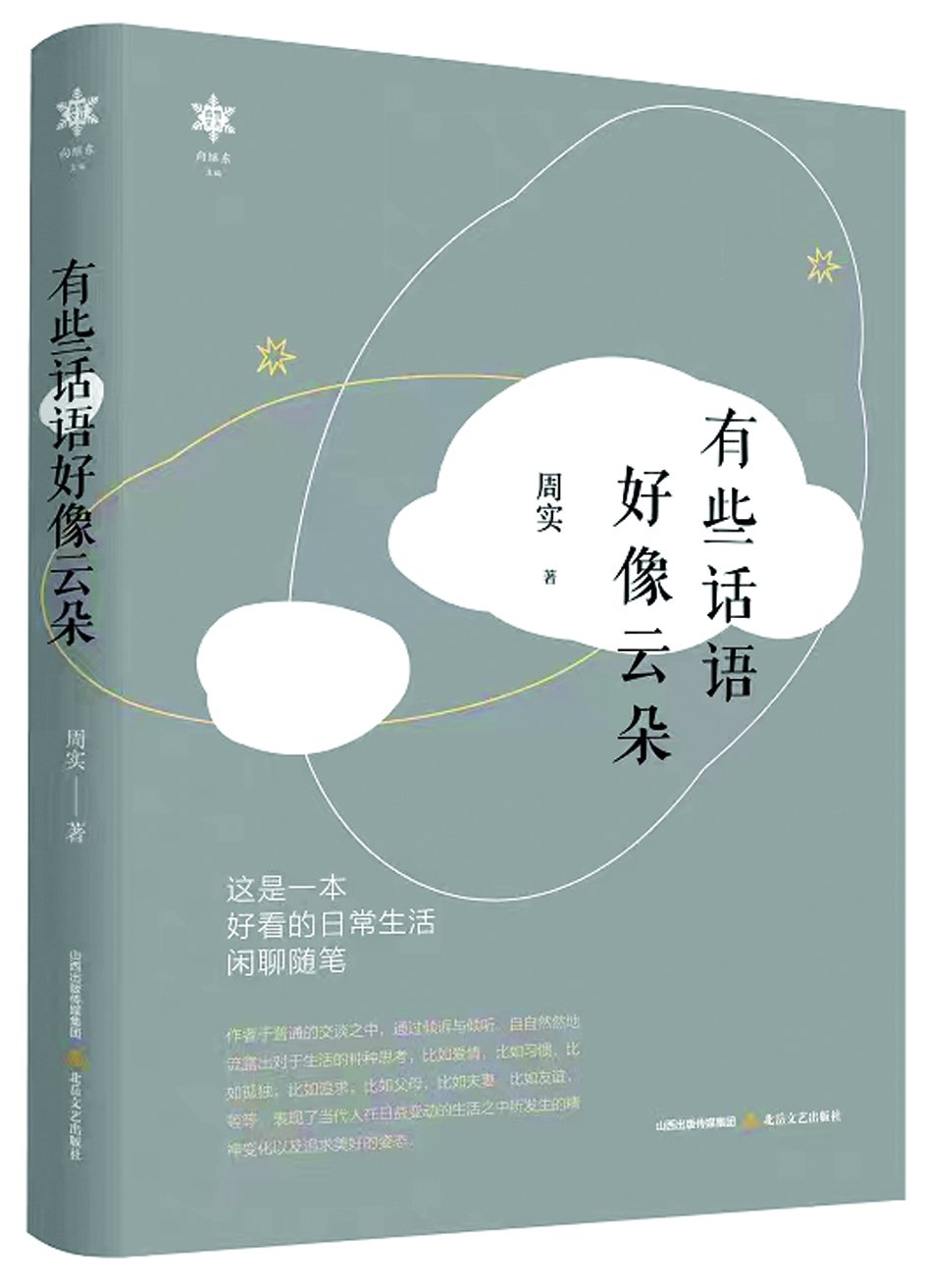“硬汉”硬汉、痴情汉和“一根筋”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安徽商报的硬汉、痴情汉和“一根筋”,如果您对硬汉、痴情汉和“一根筋”感兴趣,请往下看。
■私读 《名叫月光的骏马》
◎卢一萍/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王刊
《名叫月光的骏马》是卢一萍的短篇小说选集,故事在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合曼草原、喀喇昆仑腹地的天堂湾、阿里高原的多玛和塔克拉玛干的空间里铺展。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和《尘埃落定》一样,这本集子也关注边地,充满异质感。只有在那片土地上“苦熬”过多年的人,才能如此深刻地了解那里的风物,才能有对人和事予以文学化的能力,从而深入到那些塔吉克人、维吾尔人、汉人的内心,塑造出诸多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
选集中的女性,除了一个军人外,都是少数民族的牧羊女。在爱情中,她们比男性更为大胆,更为主动,更没有束缚,总是行为的邀约方。男性的类型则更为丰沛一些。有少数民族男人,也有汉族军人。但总体而言,可以分为硬汉、“一根筋”和痴情汉。
《最高处的雪原》中的阿廷芳便是个硬汉。在一场暴风雪中,十一匹军马逃跑了,阿廷芳决定去找回。要知道,在世界屋脊,人马是相互倚重的,没有它们,没有马,人便很难生存。那是零下40多摄氏度,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暴风雪把连队变成了孤岛。阿廷芳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艰难寻找了五天,吃光了干粮,差点陷入绝境,终于找到了幸存的六匹军马。
《快枪手黑胡子》中的大功营营长王得胜也是一条硬汉。他在抗日战争中跟鬼子拼刺刀右脸受伤,要是刺刀再偏一点,就取了他的性命;又在林南战役中失掉了左臂,空的袖管在沙暴中呼呼作响。这让他的“眼睛里还残留着一股杀气,他的眼光锋利得像一把带着血迹的刺刀”。他率部队在索狼荒原垦荒,沙暴肆虐的时候能把车窗敲碎,把他们活埋。在那样的天气里,王营长还能用独臂跟土匪黑胡子周旋。
这让人想起杰克·伦敦关于荒野的小说,那些在与自然的搏杀中爆发出强大力量的人,个个都是英雄、硬汉。在当代文学里,我们见惯了零余人和失败者,他们无力跟自然、跟生活和命运对抗,沦为被算计却无力还手的小人物。而阿廷芳和王得胜则续上了硬汉形象的传统,与《野性的呼唤》《老人与海》等作品遥相呼应。
“一根筋”自然归属《哈巴克达坂》中的凌五斗。这是个充满激烈细节的故事,卢一萍却用幽默的笔调写来,让人莞尔之余,深受震撼。凌五斗的一根筋,在某些地方可以理解为执着,比如他一个人坚持去挖掘被埋的战友。通常也会被理解为傻,不识时务,没有昧着良心,去获取切身利益。对“傻子”的书写并不是从卢一萍开始的,《喧哗与骚动》《傻瓜吉姆佩尔》《尘埃落定》《好兵帅克》等等已经创造了美学范式,但卢一萍却赋予了“傻子”新的内涵,凌五斗以一己之力与谎言的世界、俗世的世界、权利的世界对抗,维护着心中的执念。卢一萍实际写的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卢一萍还是写爱情的高手,他塑造了一批痴情汉。《北京吉普》中的“我”深恋着娜依,不惜与县长的儿子决斗,哪怕被关进监狱,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名叫月光的骏马》中的“我”为巴娜玛柯踏上了寻爱之旅,但败给了县城富二代阿拉木,有钱人终成眷属。与《北京吉普》相比,一喜一悲,后者有了明显的痛感。《克克吐鲁克》中“我”深爱的古兰丹姆为了承担家庭责任,嫁给了家有羊群的残疾人,“我”大为悲伤,抱着马脖子大哭。《银绳般的雪》中的凌五斗虽然傻乎乎的,但仍然痴爱着德吉梅朵,最后被连长棒打鸳鸯。《七年前那场赛马》中,卢克、马木提江是好朋友,他们都深爱着萨娜,两人都希望萨娜能生活幸福。卢克担心萨娜远离故土和亲人,希望她嫁给青梅竹马的马木提江;马木提江则希望萨娜能跟着卢克去他想象中天堂一样的城市里去过现代而美好的生活。最后,他们决定用一场赛马来决定萨娜的归属。时隔七年之后,随着真相显露,小说在爱的疼痛中走向和解。
进入21世纪,爱情不知为何在小说中消失了,从《诗经》开始的传统出现了断裂,世界文学里也不再有《呼啸山庄》《简爱》《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爱情。当小说写作只面对物质、身体和欲望时,《不谈爱情》一语成谶。对爱情的书写其实是相当考验作家写作功力的,很多作家也许是知难而退。但卢一萍却从俗世中超拔而出,用雪水洗尽纤尘,冲洗爱情,让它们隆起为天堂湾一样的高度。
小说是关于人物的学问。《名叫月光的骏马》塑造的人物群像,面目各有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尽量避免了简单化和扁平化。卢一萍用暴风雕塑沙丘的手法,刻画了一批棱角分明的人物;又用暴风雪塑形山河的方式,将那些人物的粗粝处进行雕琢,使之圆润饱满。有了这些人物群像,这本集子就像月光一样澄澈,像银绳般的雪一样闪光了。
好了,关于硬汉、痴情汉和“一根筋”就讲到这。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科技金融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相关文章
- “尔森”用心倾听大自然的神秘邀约
- “考生”硕士统考发布报名提醒 考生需及时自查,抓紧时间修改
- “合肥市”“柿柿如意,柿如破竹”…… 高三学子“花式解压”
- “肌肉”磁铁刺激疗法可“对齐”肌肉纤维
- “低价”第15个双11:电商巨头争夺“最低价”、取消预售、开放生态
- “犯罪嫌疑人”湖南新化砍伤一对夫妇的犯罪嫌疑人落网,4人涉嫌窝藏罪被批捕
- “中国移动”中移动市场详情:合作伙伴大会重要发言及发布、反诈、5G应用获奖
- “血液”简单的血液检查调整可使重症监护治疗更安全
- “南充市”落马公安局长收受财物1365万被判7年:悔称利欲熏心,“金钱大厦”瞬间倾覆一生毁灭
- “高粱”河南固始有执法人员带人偷高粱?当地回应:涉事人员为行政执法大队人员,正调查
- “孩子”一生的功课
- “诗人”带着大海散步的人
- “的人”以乡村和航天为背景,电视剧《离星星最近的人》在四川凉山开机
- “存款”DT研究院:调查显示53.7%年轻人存款不足10万
- “的人”Shopify旺季调研:74%消费者预计将比去年支出更多
- “成都”想现场给伍佰唱歌的人太多,伍佰巡演成都站再加一场
- “苹果”段永平:假装自己懂投资是很危险的
- “手印”“千眼天珠”里的95个手印
- “自己的”当代投资人 “不务正业” 图谱:主业干不出成绩,副业得搞起来呀
- “残障”立体版成都大运会“显眼包”里,是一群残障阿姨们的爱与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