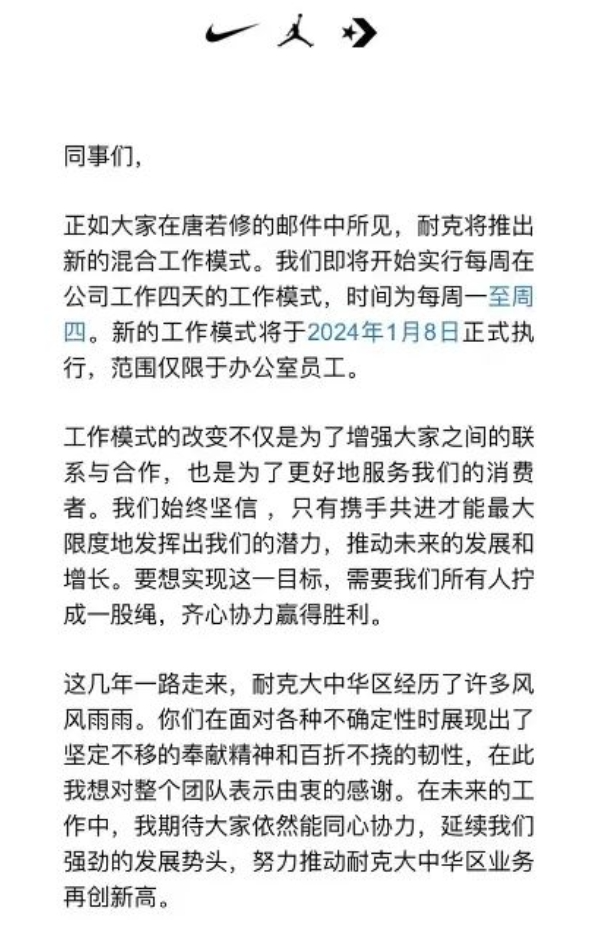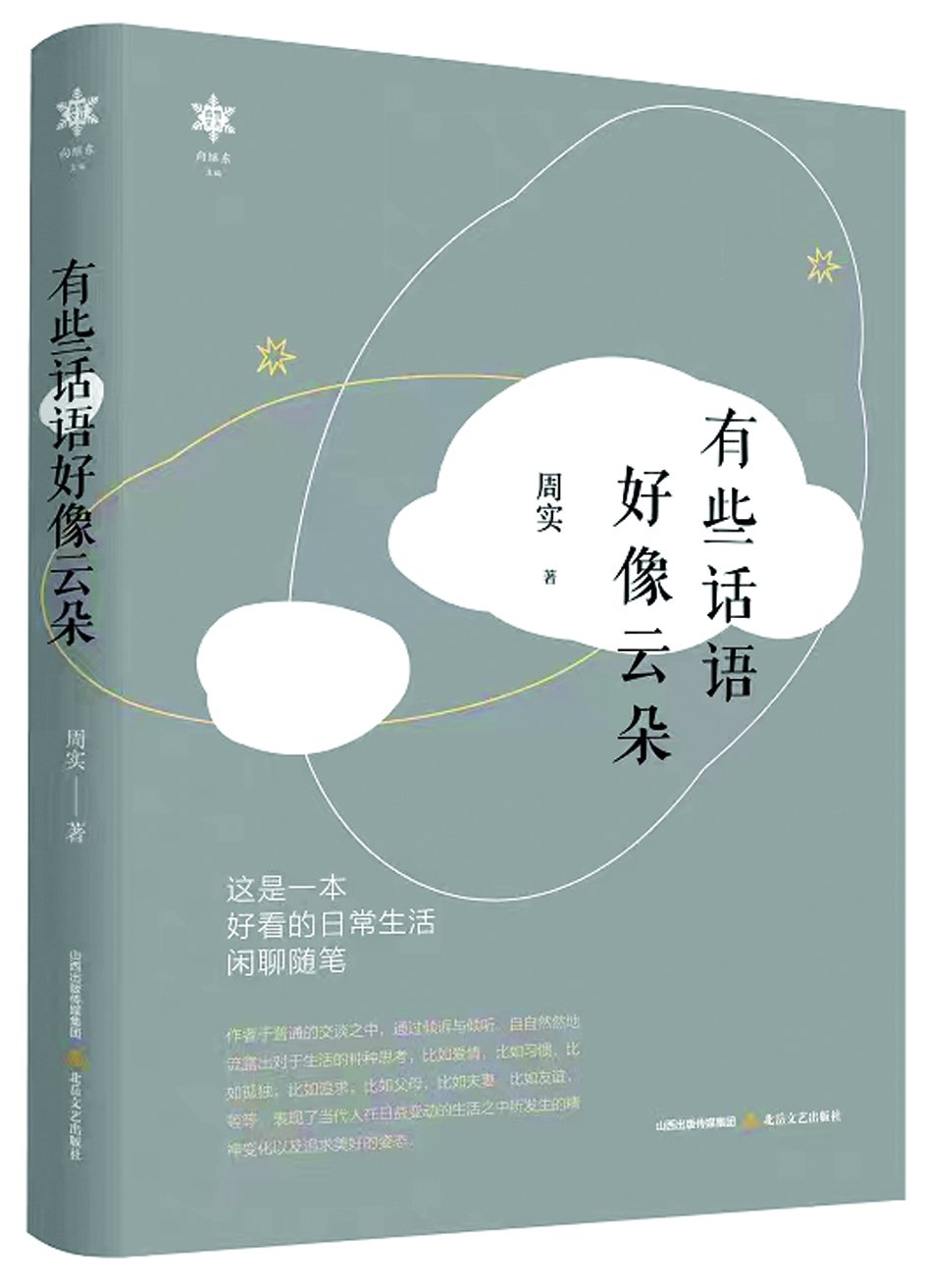“重庆”勘探一位作者的写作“前史”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安徽商报的勘探一位作者的写作“前史”,如果您对勘探一位作者的写作“前史”感兴趣,请往下看。
■读后 《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
◎宋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约十年前,重庆小说家贺彬为宋尾小说集《到世界里去》写过一篇评论。贺彬在文中指出,集子里的《生日快乐》一篇庶几是“整本书的前传”,因为小说既没有落脚于作家长期生活的城市重庆,也不曾发生在他的故乡天门,而是“一个中间地带,一个悬置的时期”。读了贺彬的文章,我又重读了《生日快乐》,其中确已可见宋尾今天不疾不徐的语调。并且,那在故事里嵌套故事的写法,同样也在日后愈发精熟。
迄今为止,宋尾的两部长篇与三部小说集,几乎无一例外以重庆为背景展开,然而,我也正由此诧异这些“重庆故事”与一个“重庆作家”的诞生———他是如何变得比一些本地作家对这座城市更有感觉?为何他没有在自己的小说里留下任何故乡的雪泥鸿爪,甚至连影子也没有?宋尾对怀旧的清除看起来是如此彻底。这种诧异,直至读到作家晚近以来的两个作品《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下汉口》,方才堪堪纾解。对于这两篇将目光转向江汉平原的小说,笔者的意图在于探究其中那个“隐含作者”的前史。
在《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里,宋尾克制住了他一直以来擅长讲故事、造悬念的能力,平淡地讲起一件小事:小鸥回到了“我”生活的湖北小城。两人相识,源于小鸥曾参与“我”的发廊生意,她在此滞留一月,离开前向“我”许诺会带来两个年轻一点的姑娘。“我”知是客套话,故并未挽留,而且后来“我”也因此进了拘留所。两人的重逢发生在“我”从拘留所出来后不久,彼此境况一仍其旧。可是,后来的情节又透露出“我”的改变:很快“我”便从众人的狂欢脱身。“我”珍重与小鸥的感情,不愿再次领受轻率的结合;离开旅馆维护了“我”最低限度的尊严,至于这点尊严能为那一潭死水的生活带来什么,“我”并不知情。十二天后,一张异地的诗稿汇款单让“我”有勇气重新面对小鸥,却被告知那晚他们已为治安队一网打尽。《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同宋尾以往披着侦探小说外衣、深描城市人心的作品毫不相同。如果这篇小说也有谜底,这个谜底是直到结尾才被揭晓的:以上乃十数年前的往事。
很难说是不是过往的创伤让宋尾仅只写下了这不多的“江汉旧事”,但也让他在更多时候下意识地选择隐匿自身的文学源头。《下汉口》一样是以当下为跳板,以反顾而收尾:三十年后,姑姑倏然率领她的老年打鼓队造访“我”位于重庆的家,她高兴地向伙伴展示这个有出息的侄子。自然,两人也谈起“我”和父亲三十年前在汉口的那次迷路。姑姑笑言父亲是个“苕”,“从来就不晓得问个路”,至于“我”,心情不免有些沉重,因为“直到父亲去世,我们再也没有这么单独而亲密地走在一起”。何况那段百感交集的旅途也不曾缓解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总之,“我们这一生都在对抗。我一直梦想着逃离”,直到“我”前往重庆,变成姑姑口中“神奇的侄子”,也直到父亲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离去,徒留作为人子的“我”思索这段从未讲和的关系。
相较毫无保留的展示,父子关系在作者第三部小说集的《大湖》一篇,还有另一重变体。《大湖》这篇小说纯粹是以一连串梦境的描述与对这些描述的否认完成的拼图。刘警官的讲述,以他自身的“现实”经历与将这种经历指认为不可靠的梦结束;作为主人公的“我”,又经历了他人对“我”关于刘警官回忆的回忆的否定。如果前者是现实被指认为梦境,后者就是在指认梦境的现实中又一次地被指认为此乃关于梦境的梦。既然如此,是否还存在一种真实呢?曾和父亲下汉口的人子在成年后时常分不清哪一个父亲的形象才是真的,而《大湖》的结尾回答了这个问题:朋友们不仅否认了“我”关于刘警官的记忆,也把“我”那晚说起的一件异闻在电话中重述于“我”。末了,“我”怔怔握着电话,在镜中又看到了父亲独有的姿态、神情与犹疑。以笔者之见,宋尾这些作品既容纳了对真实并不存在的惶恐,其主旨也十分接近福克纳《修女安魂曲》中所言“过去永远不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
综上,或可谨慎立论如下:那始终在宋尾“重庆故事”中回荡的基调、不变的底色、察觉的真相,其源头都是一位落魄诗人在“走向世界”以前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的希望与幻灭的二重奏。
·徐兆正
好了,关于勘探一位作者的写作“前史”就讲到这。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科技金融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相关文章
- “考生”下半年自考即将开始 省考试院发出温馨提示
- “父亲”父亲的眼神杀
- “这是”自内耗到自洽
- “大桥”G3铜陵长江公铁大桥先导索过江
- “某甲”父亲被羁押继母要离婚,未成年女儿谁来抚养?法官多方努力,难题解决了!
- “亚马逊”哪些以色列芯片公司已被美国企业收购?
- “结构”结核杆菌致病机制获揭示
- “装修”装修公司老板明知公司亏损仍吸引客户签合同,骗取上百人700余万,被判11年
- “射电”穿越80亿光年的快速射电暴源于一场“星系交通事故”
- “必胜客”必胜客最黑暗的料理来了
- “父亲”父亲的眼神杀
- “营业厅”岁岁重阳 双向奔赴的联通助老情
- “科研项目”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科研项目终止的公示
- “科研项目”重庆市科技局公示第四批科研项目评审验收结果
- “重庆市”重庆发布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项目申报通知
- “北碚区”重庆一高层底楼住户私挖“四室一厅地下室”,北碚区住建委:已派人前往现场查看
- “精准”预计总投资3亿,重庆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来了
- “北京现代”降价11亿!北京现代销量暴跌卖厂止损:重庆工厂再次挂牌出售
- “城市”中秋国庆消费最火城市出炉:重庆夺冠 拉萨爆发
- “女童”上海4岁女童走失,家属最新回应:父亲回到原地未找到人,几分钟后孩子疑被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