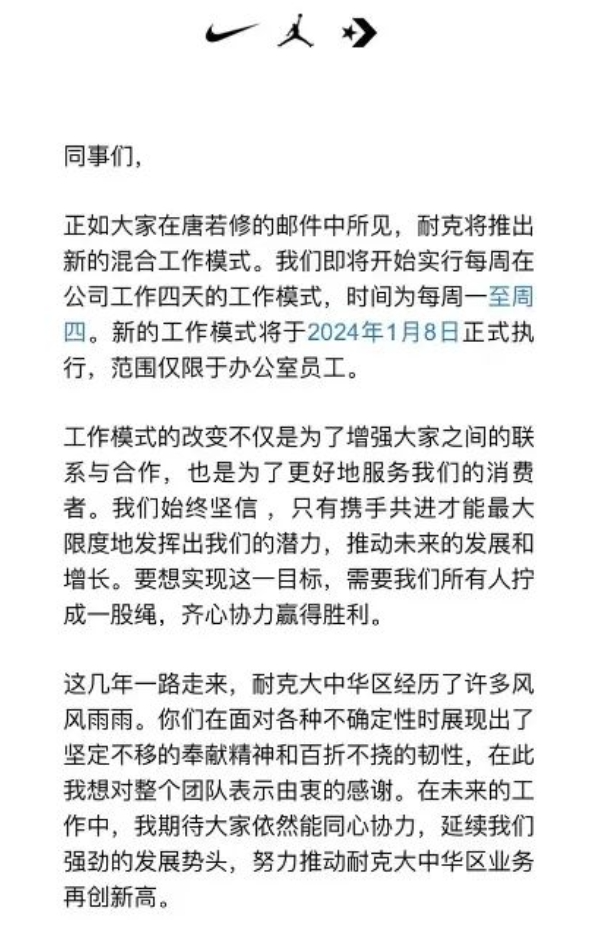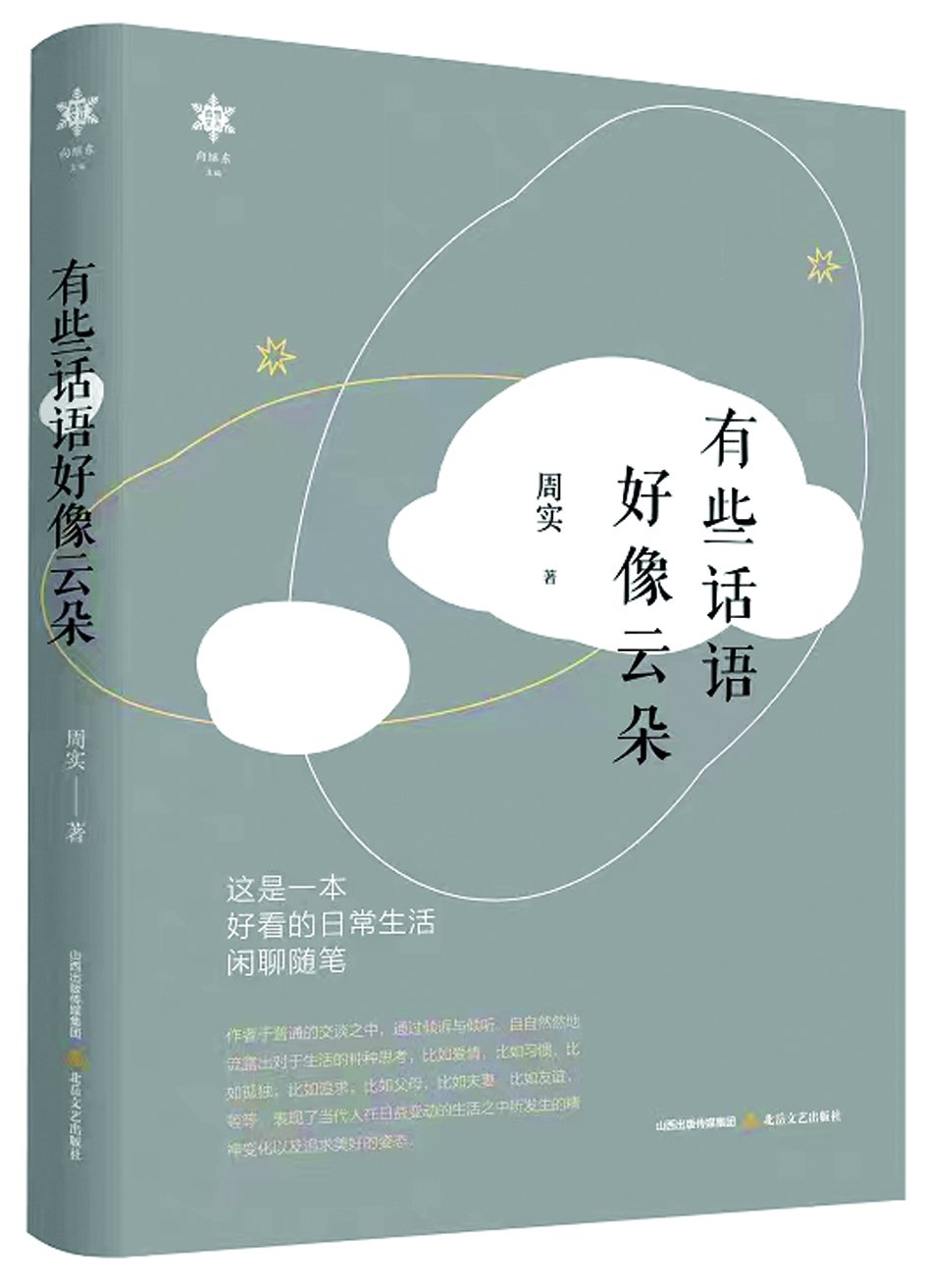“饺子”饺子是味药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安徽商报的饺子是味药,如果您对饺子是味药感兴趣,请往下看。
■美食
刘亚荣
小时候被饺子撑到过,高烧,差点死去。父亲屡次说起这事儿,说我站在桌边左右手抓着饺子吃。那时,父母盼儿子,妹妹生下来,叫“多”。经过这次意外,妹妹的大名才叫起来。古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感谢饺子。
大概除了父母,天底下再没有人吃过馅里有煤油的饺子。
那年我十来岁,忙碌了一年的父母,终于可以盘腿坐炕上包过年的饺子。那时虽穷,却讲究,初一初二甚至破五的饺子都要包出来,三十晚上也算大工程。毡条已经翻起来,案板和馅盆都在炕上,昏暗的煤油灯在靠东墙的灯龛里,母亲指派我把灯挂到屋子中间。我脚下一滑,一个趔趄,灯油都撒到饺子馅里。母亲忍住没打我,自己却忍不住难过地哭起来。犹记二月二的时候,父母单独包了放了一个月的带煤油的馅.母亲说,没事,死不了人,煤油治虫子(蛔虫)。
那时吃顿饺子也不易。大人们忙着生产队的活,也没多少白面可用。分田到户后,日子才舒展。每次我从距家几十里地的单位回来,母亲会急火火跑到园子里摘来西葫芦,剁上几瓣蒜,这样的饺子就有了韭菜的味道。下饺子的时候,母亲会念叨“南边来了一群鹅,扑棱扑棱下了河……”这白生生的饺子,真像一群在汤池里仰俯的白鹅。
饺子和扁食一样是敬神的供品。大年初一,母亲是无比虔诚的。她按照神三鬼四的传统,把第一笊篱饺子,三个一碟供在天地龛和灶台上,敬天地神仙,四个的给祖先,并在父亲点燃鞭炮时,点燃一束香。年复一年,母亲的祈愿并没有改变什么。那个三十晚上,老鼠闹腾得厉害,父亲几次冒着寒气披衣到对屋查看初一的饺子。起五更时,满满一篦帘饺子,居然一个不剩被老鼠拖走了。自此,母亲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她觉得那些祈愿,没有一点作用。
有个阶段,最不爱吃饺子,尤其婆婆包的饺子。饺子下到锅里,棒子铺面像稀粥。大白菜下来的时候,婆婆用青白菜帮子做馅,放一点干粉头,香油都舍不得放。六十出头的婆婆公公显得老迈,天天吃白面,二老觉得知足。每逢集日,我会称点肉或买点鱼,公公不舍得,劝我攒钱,省着花。二老的生活改善,就是大白菜、带一点油星的饺子。每天晚上,不是饺子就是饺子粥。我常常吃不下去,用筷子扒拉着饺子发呆。
公公去世时,正是伏天。供桌上,有供品,一盘四个饺子,伴着一炷香,以及烧纸的味。更多的饺子,放在瓦盆里,苍蝇嗡嗡着叮上去。饺子成了摆设,成为活人对逝者最后的慰藉,最后的烟火,悲伤的味道。如今,再没人用饺子当供品,节省了时间,简化了程序,悲伤也风一样,旋一个旋,滞留一会儿,就无情地刮过去。
婆婆也曾来市里,住过很短时间。她消化不了鸡鸭鱼肉,她的胃属于乡村,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不会问饺子的来历,更不知道扁食,她遵循的是朴素的家庭主妇的为人之道。公公的大男子主义,或许这是我强加给老人家的,他们不懂得什么主义,执着地吃苦受累,为了给孩子们盖房子娶媳妇,陷在种地盖房的循环里。能吃上肉饺子,是他们那辈人的心愿。
时光的皱褶里,饺子的影像并不少。喜欢过年,一家十几口子,挤在一间屋子里吃团圆饺子。这样的事自婆婆去世画上了句号。离乡多年,越发强烈意识到,饺子吃的是团圆,是家的感觉。饺子皮包的是酸甜苦辣,融的是五味的情感,是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祈愿。
我在外地吃过无数饺子,还是感觉自己包的合口味。
每次包饺子,越发体会到母亲的不易。早先是缺乏食材,现在是面对挑剔的口味。我每次包饺子至少两种馅料,甚至三种。也不觉麻烦,看到家人吃得喜欢,甚是欣慰。
余下的面和馅,我还是包成饺子,做成饺子粥,它有个让人喜欢的名字——小鱼钻沙子。充满文化味,让俗常的食物升华。
北方饺子与南方水饺不同,不仅是馅的醇厚与清淡,是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的差异,如今我爱吃饺子,饺子是团圆的象征,打破孤独坚冰的利器。
好了,关于饺子是味药就讲到这。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科技金融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相关文章
- “小行星”我国2030年前后 实现载人登月
- “都是”A股的觉醒之年!
- “孩子”一生的功课
- “益康”倍益康上市几个月收入净利都大减 市值仅几亿 创始人张文有啥办法?
- “科幻”嘉宾共话科幻的未来:被视为“珍贵市场”,中国科幻正青春
- “灯会”红星观察|自贡灯会走出“春节舒适区”:首次试水中秋国庆主题灯会火出圈背后
- “华为”新麒麟全面替代!曝华为正在清理骁龙机型库存:掀起全线新品的“洪流”
- “鸟类”评论丨大楼玻璃贴膜防鸟撞,城市的天空如何助鸟自由飞翔?
- “同济大学”四川“无臂青年”彭超参与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曾用脚写字考上同济大学研究生
- “模型”人工智能公司OpenCSG发布大模型开源生态社区“传神”
- “万元”中大型纯电SUV再添一员:昊铂HT开启预售
- “小时”抖音“小时达”上线独立入口 将动谁的奶酪?
- “屏幕”消息称iPhone 17系列屏幕有重大升级:“胶囊屏”时代终结
- “订单”9 月网约车行业共收到 7.93 亿单,享道出行订单合规率最高
- “惠普”惠普亮相Tech G 2023,觉醒行业新生态
- “学报”患病后,他高薪聘请研究人员,“没有一个人工作超过3个月”
- “假期”打工人的八天假,比上班还累
- “女儿”吴艳妮以小组第一晋级亚运会女子100米栏决赛 母亲:状态不错,希望决赛发挥得更好
- “基金”“冠军基金”博时鑫瑞清盘 还有哪些明星基金被大比例赎回?
- “的是”硬刚Vision Pro,Meta Quest 3 头显发布,售价500美元,10月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