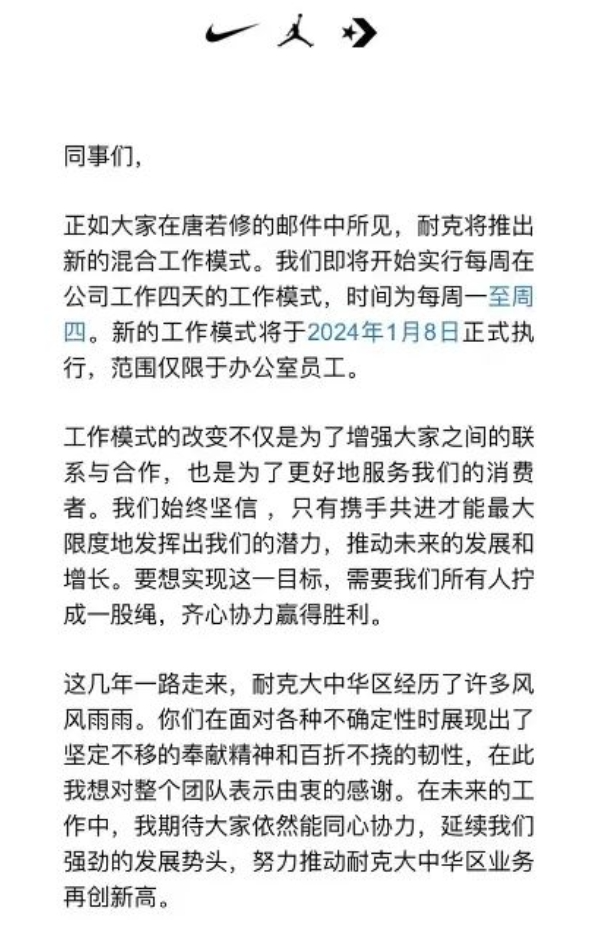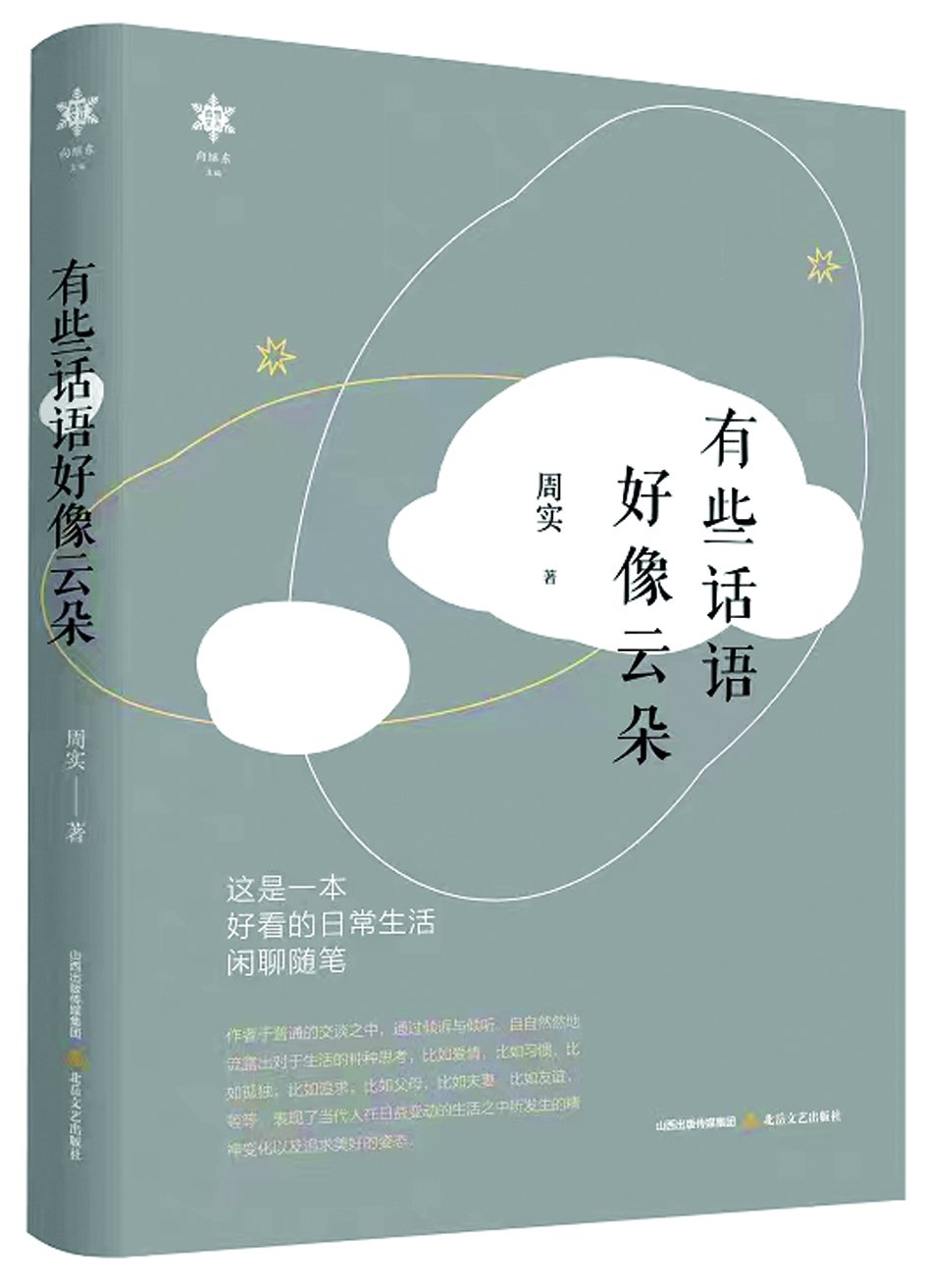“父亲”父亲唤着我的乳名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分享来自安徽商报的父亲唤着我的乳名,如果您对父亲唤着我的乳名感兴趣,请往下看。
胡文燕
“38床患者家属出来一下!”主治医生将我喊到住院部过道走廊,面色凝重地告诉我,患者属于突发性急性脑梗死,病灶虽然不大,但是在主脑干桥脑位置,情况不太乐观,也就是通常说的中风,你要有思想准备。
如同从空中跌落,我的心霎那间沉入了谷底,靠在走廊的墙壁上呆愣了好久。一个活动自如的正常人,一生都没住过院的健康人,怎么就突然中风了?而且经过医生风险评估,说是没有做溶栓手术的必要了,这就意味着恢复正常的可能性机会非常渺茫。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又坐到了病床跟前。父亲裸露在外的四肢关节处,一圈又一圈紫红色的淤伤,触目惊心,不忍直视,结痂的伤口微微凸起,渗着一丝丝血水,仿佛一双满含幽怨的眼睛,涌着伤心的泪珠,无声地诉说着4月23日清晨,病发时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
住院头一个星期,父亲无法接受自己左边肢体已经瘫痪的现实。有天清晨五点钟左右,他悄悄地将能够活动的右腿伸到病床的边缘,整个身体顺势往下蹬。待我察觉到声响,他右腿已经着地,毫无知觉的左腿悬在床沿。我大吃一惊,慌忙喊醒隔壁陪床家属,合力将父亲抬到病床上。很显然,他想自己下床验证一下是否还能行走。如果不是发现及时,再次发生坠床事故,后果将不敢设想。我后怕不已,安抚好父亲的情绪,趁着护士查房间隙,和护士尝试着将父亲搀扶到地面,那条毫无知觉、不知道抬脚迈步、不知道踮脚进退的左腿,无力地拖在地面,犹如一件毫无价值的附属物。那一瞬间,父亲似乎默认了现实,低下头,轻声叹息,沉默无言。我不忍心直视他那双空洞无助的眼神,心口仿佛被钝器重伤,喘不过气,一阵阵生硬的疼,撕扯着我的全身神经。失望向我围拢而来,空气也湿重了起来,全身似触碰蛇信子般透凉,彻底击碎了我心底仅存的一丝侥幸。我知道,我不能垮,我曾是父亲眼中的苗,现在是父亲心中的树,我要坚强,在父亲面前,尽量强颜欢笑,增强父亲坚持康复的信心和力量。
常年的寡居,让生性敏感的父亲愈加孤僻沉默,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父亲嘴里偶尔口齿不清地念叨着,含糊不清,我贴近他的脸庞,连估带猜应该是说肢体没劲。除了这种无助的低声细语,他整日都沉默无言。我明白,我累的是身,他垮的是心。我怕这样下去会彻底丧失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便撑着疲惫的身体,和他拉拉家常,分散注意力,一遍又一遍地鼓励他,一定要加油哦!等康复了一起去公园散步遛弯。父亲难得露出了笑脸,久违的笑容驱散了心头的乌云,也让压在我心头的巨石稍微地放下了一点。
二十天过去了,按照惯例陪护,安顿好父亲的晚餐、用药、按摩、洗漱、擦身等琐事,终于缓了一口气,躺在约五十公分宽的陪护床上。凌晨约一点左右,耳边隐约传来呼唤声,我想应该是幻觉。我翻了个身继续睡,然而呼唤声却一声比一声清晰,一声比一声急促,竖起耳朵细听,没错!是父亲,在唤我的乳名!我睡意顿消,噌地一下就起来了。这是父亲中风以后,第一次完整清晰地喊出我的名字,我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涌上心头的开心、欣慰将数日来的茫然无措、心酸无奈驱逐了一半。二十天的守护终于得到了回应,二十天的治疗终于有了一线希望。
中风的后遗症很多,在运动、感觉、吞咽、语言、平衡、睡眠、二便上都存在障碍。铺展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千山万壑的崎岖之路,我需要以铁杵磨成针的恒心和决心,带着父亲一起加入到康复锻炼的大军,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午夜时分,脑海里响起父亲那一声声呼唤,再苦再累也值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声“爸爸”可以呼唤,还有一人唤我乳名,这种感受,唯有经历者才有深切体会。幸福,原来是那么简单,简单到能听到亲人唤我的乳名,简单到亲人的一日三餐能够自理,简单到还有亲人可以陪伴……
好了,关于父亲唤着我的乳名就讲到这。
版权及免责声明:凡本网所属版权作品,转载时须获得授权并注明来源“科技金融网”,违者本网将保留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的权力。凡转载文章,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相关文章
- “小行星”我国2030年前后 实现载人登月
- “都是”A股的觉醒之年!
- “孩子”一生的功课
- “益康”倍益康上市几个月收入净利都大减 市值仅几亿 创始人张文有啥办法?
- “科幻”嘉宾共话科幻的未来:被视为“珍贵市场”,中国科幻正青春
- “灯会”红星观察|自贡灯会走出“春节舒适区”:首次试水中秋国庆主题灯会火出圈背后
- “华为”新麒麟全面替代!曝华为正在清理骁龙机型库存:掀起全线新品的“洪流”
- “鸟类”评论丨大楼玻璃贴膜防鸟撞,城市的天空如何助鸟自由飞翔?
- “同济大学”四川“无臂青年”彭超参与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曾用脚写字考上同济大学研究生
- “模型”人工智能公司OpenCSG发布大模型开源生态社区“传神”
- “父亲”父亲的眼神杀
- “女童”上海4岁女童走失,家属最新回应:父亲回到原地未找到人,几分钟后孩子疑被卷走
- “老人”失踪二十多年 父亲终于找到了
- “父亲”秋读张爱玲
- “课本”书香里的开学季
- “韩国”韩总统92岁父亲去世,韩媒:尹锡悦仍将如期赴美参加美日韩峰会
- “父亲”父亲辞世后 天才译者金晓宇的“独行”人生
- “健康”鸿茅药业携手国大益源大药房开展公益活动
- “孩子”成长过程中,爸爸的陪伴有多重要?
- “父亲”男子驾船出海离奇身亡,其女悬赏50万追凶,疑似肇事者为赏金主动投案